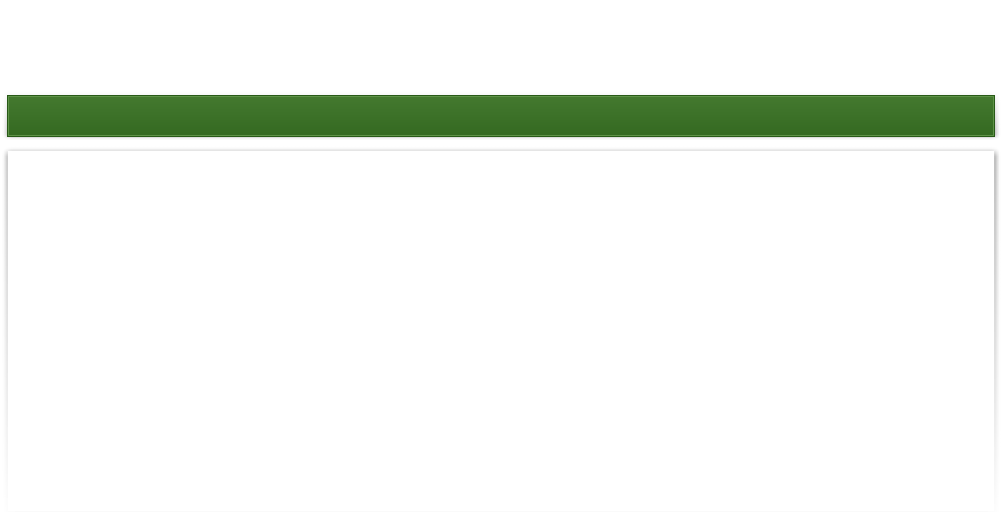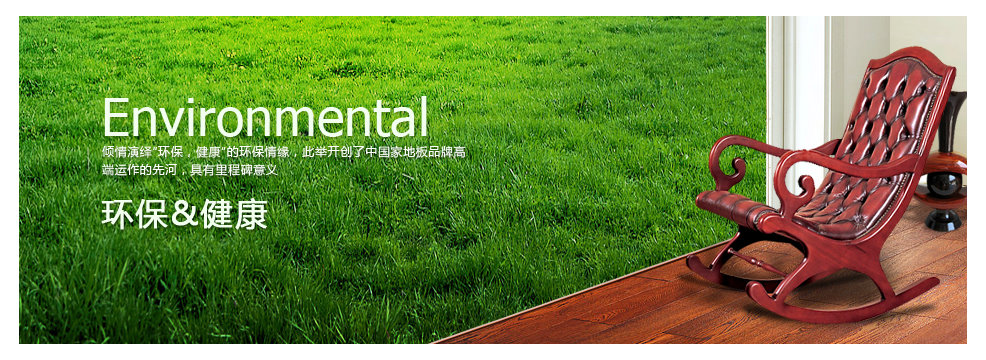在十二生肖中,虽然蛇的形象及故事不比其他动物大约最生不逢时。鼠和猪的境遇都比蛇好,传统年画有老鼠娶亲、肥猪拱圈的题材,但无论在年画、民歌或童谣中,都基本看不到蛇的影子。
但蛇自有蛇的传奇。宠蛇、耍蛇、祭蛇在历史上并不罕见。最值得骄傲的是,鼠和猪都和美女没有关系,而白娘子乃是白蛇所化。
题作南朝梁人任昉所撰的《述异记》书中,有《蛇市》一条,说:“扬州有蛇市,市人鬻珠玉而杂货蛟布。”蛇市的得名,是有人在此卖蛇、买蛇、耍蛇,而后才形成市场的。不过南朝时的扬州是指金陵,即今天的南京,而不是现在的扬州,当时扬州称广陵。
可是扬州也早就有人把蛇当作宠物了。唐人裴铏《传奇》中有《邓甲》一篇说,唐代宝历年间,茅山道士峭岩有“禁天地蛇术”,据说用这种法术能使蛇听从命令。《邓甲》写道,扬州有人因为耍蛇而成为富翁:“时维扬有毕生,有常弄蛇千条,日戏于阛阓,遂大有资产,而建大第。”唐朝的维扬,当然就是今日的扬州。所谓“阛阓”是指市街商铺。这位毕生养了千余条蛇,每天在闹肆耍蛇,其场面之热闹,收入之丰厚,是可以想见的。他也一定是熟悉蛇性的内行。
在远古时代,人们见面问候的第一句话是:“无它乎?”“它”就是蛇。蛇在最初是令人恐惧的一种动物。不仅在中国,在世界各地似乎都是如此。人们熟悉的《圣经》故事里,那个在伊甸园引诱亚当、夏娃偷吃禁果的恶魔,就是化作蛇形的。为了讨好蛇,以便得到蛇的保护,先民们便有了蛇图腾崇拜。中国古代“百越”和“三苗”等一些部落,都以蛇为崇拜对象。摩尔根《古代社会》一书里,提到许多以“蛇氏”、“黑蛇氏”、“响尾蛇氏”为名称的氏族或部落。
在汉代的百戏中,已经有“弄蛇”的节目。弄蛇,即耍蛇,也即蛇戏。从汉代画像石描绘的“弄蛇”场面,我们能够约略知道汉代蛇戏的情形。山东嘉祥武氏祠有这样的汉代画像石:其一,中间设一台,台上盘一蛇,右方有人,高冠后垂,为弄蛇者;其二,中间一人,有大蛇绕身,左右各一人,手执锤状物,面蛇作舞状,三人均为弄蛇者。浙江海宁也有汉代画像石,绘数人作相朴、拳击状,中有一条巨蛇,盘旋腾空,作舞蹈状。
古人认为蛇能被人操纵,是由于它能听懂人话。这类趣事,不乏记载。如宋人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说,广西人喜食巨蟒,每见之,即诵“红娘子”三字,蟒辄不动。且行且诵,以藤蔓系其首于木,然后刺杀之。清人陈鼎《蛇谱》说,蛇不但能够听懂人话,蛇自己也能说人话。如有一种“唤人蛇”,产于广西,伏于草莽间,有行人走过,它就喊道:“何处来?哪里去?”其口音如同中州话。
淮扬一带多水,有利于蛇的生存,所以养蛇的人也多。宣鼎《夜雨秋灯录》说,淮安周木斋,善书嗜饮,疏狂不羁,最喜养蛇,床头厕上,到处是盘曲的蛇。“夏日,先生怯暖,两臂所盘者蛇,腰际所围者蛇,赤足插瓮中者亦蛇也。”如果家中来了不受欢迎的客人,他心生厌恶,只要吹一声口哨,群蛇立刻游至,“客狂呼大奔,往往有惊破胆者”。
《清稗类钞》中有一篇《三大王捕蟒》,说扬州邵伯东边有个小村,住着农民十数家。咸同年间,村外小庙中有巨蟒盘踞,村中鸡犬时有丢失。夏日,有牧童坐牛背,徜徉游戏,大雨忽至,急忙进庙躲避。才进庙门,就见目光如电,长舌如叉,有斗那么粗的巨蟒,自梁上垂下,牧童大惊而逃。从此后,村人耕牧,都不敢近庙,庄稼亦渐荒废。人们想尽方法也不能驱除蟒害。过了一个月,忽有一少年过此,持三尺剑,跨千里马,对村人说他能治蟒。少年先到小庙转了一周,说:“这个容易。”就命村人拔尽东南大道上的蔓草,凡十里许,不留一茎。次日,少年策马来,入庙斩蟒,蟒受重伤,追噬少年。少年疾驰而去,巨蟒奋力追赶,终因大道上蔓草尽除,巨蟒游动不快,但大家都为少年担心。“忽见尘起如雾,一骑疾驰以来,鲜血沾染殆遍,视马上人左提蟒首,右握宝剑,众皆欢呼争趋迎之。”原来,少年终于为民除了蟒害。村人将蟒首秤了秤,重达六十余斤。
过了几天,捻军过境,其头目人称“三大王”。村人一看,正是那个除蟒的少年。不料捻军被官军打败,“三大王”被捕。第二天,少年首级悬挂军门,村人见之,痛惜不已。这个“三大王”应是扬州一带的驯蛇能手。
从前古运河边有许多龙王庙,龙王的原型其实是蛇。古有“龙蛇之变”一语,出自《庄子》,原是庄子回答弟子的一段话:“一龙一蛇,与时俱化。”龙与蛇外形相似,龙蛇之变比喻做人要能屈能伸。为蛇时要蛰伏地下,与蝼蚁为伍,为龙时要腾飞长空,与鹰隼结伴。
在扬州人崇拜的动物中,龙蛇也是时常变化的。前人记载曾经亲眼见过龙。民国时蔡云万《蛰存斋笔记》有一篇《大王与将军》写道:“清江浦系前清漕运总督驻扎地,向为南北水陆要冲,漕督所掌者以粮运为最重。相传粮艘航海而来,均有神龙护送,虽当水浅舟胶,粮艘一至,运河水能陡涨若干尺,舟即畅行无碍。幼时习闻此语,疑为怪诞不经。年未冠赴淮安应府试时,先大夫锡朋公尚在堂,曾命得暇可顺赴清江浦探友,因往一游,适得见所未见,一释前疑。”接着,作者叙述了自己在淮扬运河亲见“大王”(即龙王)的情景:
粮船启航时,如果觉得胶滞难行,船主即知有异,马上到后艄探视。这时,往往会看到“大王”蟠伏在船舵的横木上。船主随即以朱漆盘呈进,“大王”即蜿蜒自游入盘。这种情景并非在一条船上出现,而是普遍如此。等到各个船主会集,问明情况,就请这些“大王”一起进入一个特大的玻璃盒内。于是报告漕运督署,用漕督的轿子和仪仗将“大王”迎入戏园,恭敬地陈放案上,任人近观。这些“大王”的颜色,大都是灰白、淡黄、栗色或黑色。书中说:“‘大王’形如蛇,无爪,长不逾尺,头有八字白痕,隐然似角。其时共十二条在盒内,立即开锣演戏。”如果人想知道各个“大王”的名字,都用签筒摇签,筒内有黄大王、何大王、杨四将军、陈九龙将军、曹将军等封号。最奇怪的有两点,演戏时,本地文武官员均往拈香,“大王”均伏而不动;惟有漕帅上香时则皆昂首蟠曲,以示不敢当受之意。戏演数出,“大王”就次第不见,不知其何时飞腾而去。蔡云万说:“予目睹如此,可谓奇矣。入民国后,客居清江军署凡九载余,辛酉大水曾有‘大王’出现一次,仅两条。僧人奉于寺中玻璃盒内,半月即自行他去矣。”
《蛰存斋笔记》所说的“大王”,就是旧时船民和官员眼中的“龙王”。人们认为龙王的出现,能够保护运河漕船的安全,所以敬之如神,不但把它请入玻璃盒中,还专门为它演戏。“龙王”在自然界肯定是没有的,所谓“大王”极有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蛇类。
关于扬州的龙王庙,清人赵翼《陔馀丛考》中《金龙大王》早就做过考证,说:“江淮一带至潞河,无不有金龙大王庙。按《涌幢小品》,神姓谢,名绪,南宋人,元兵方盛,神以戚畹,愤不乐仕,隐金龙山,筑望云亭自娱。元兵入临安,赴江死,尸僵不坏,乡人瘗之祖庙侧。明祖兵起,神示梦当佑助。会傅友德与元左丞李二战吕梁洪,士卒见空中有披甲者来助战,元遂大溃。永乐中,凿会通渠,舟楫过河,祷无不应,于是建祠洪上。”这段话说江淮一带的金龙大王庙,祭祀的其实是一位历史人物,名叫谢绪,宋末元初人。谢绪见世道混乱,隐居在金龙山。元兵入侵后,作为宋朝遗民的谢绪不愿投降,赴江而死。后来谢绪不时显灵,仗义人间,只要船民祷告,必有灵验,人们这才在运河两岸建了“金龙大王庙”。今天看来,谢绪固然是真实人物,但是船民把他神化了。运河上的航船,本来充满了危险,船民期望得到神祇的保祐,谢绪正好充当了“龙王”的角色。后来民间流传许多“金龙大王”显灵的故事,全名“延休显应分水龙王之神”。扬州运河沿岸的龙王庙,都缘于此。
几十年前,我从南京调回扬州,从家父研究扬州清曲。因苦于材料难得,不能不费尽周章。当时听父亲说过,民国时人江子余撰有扬州小曲《白蛇传》全本唱词,他亲眼见过其印本。但这种印本唯有尤庆乐先生自存一册,别无所见。从前这一孤本为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章鸣所得,后来当我父亲赴京见到章先生时,他已患上健忘症。
从听说扬州小曲《白蛇传》印本至今,时光过去了几十年,我已不再幻想见到此书。不料书友慕相中告知,他已从网上购得此书的电子本。急忙从头至尾一看,竟如获奇珍,疑心书人缘分,是否前定。
我和小女在《清水出芙蓉——扬州清曲艺术》书中,谈到江子余及其《白蛇传》:“江子余,清末民初时扬州人,扬州清曲作词家,有较高文化水平。雅爱清曲,但不善唱,一生致力于曲目与曲调的创作和改编。江子余所编的《白蛇传》和《珍珠塔》,曾由某书局出版,扬州学人王二丘先生为之作序。尤庆乐先生曾珍藏过一本江子余的《白蛇传》,1962年中央音乐学院章鸣先生来采访扬州清曲时,尤先生将此书慨然赠送。据章鸣先生回忆:江子余编的全部《白蛇传》,共用了五十余个曲牌,与通常所唱的《白蛇传》不同。惜此书未见复本。另一本书《珍珠塔》也难觅踪影。江子余所编唱本,最重通俗。据说他每写一曲,必先念给老人和妇女听,征询意见,看他们能否听懂,如听不懂则再改,直到使普通人听懂为止。在此基础上,他还要听取艺人的意见,看词调是否和谐合拍。这种立足于艺人与听众的创作理念,至今值得借鉴。”现在看到了印本《白蛇传》,我才得领略其真实的风采,也才确信家父看过此书。
封面上题“扬州小曲全本白蛇传”。书前有江子余先生肖像,面长有须,乃一老者。肖像下有邗江翟幼泉题诗:“谱就新词人竞夸,文通才调笔生花。谐音合拍歌来好,赚尽江东顾曲家。”接下来是汪二丘的《卷头语》,尤为精彩:“现在大家都提倡‘民间文学’,其实他们所谓‘民间文学’,不过是文人模仿‘民间文学’的面孔。他的思想,还是从他读的书本中出来,何尝是真正‘民间文学’。我的老友江子余先生,他本是商界中人。他读书不多,并且识字有限,他本着他的经验阅历,把社会上的一切情态描写出来,放在他所著的《白蛇传》小曲里面,这才是真正‘民间文学’呢!他做这个小曲的时候,念把妇女和小孩子们听,他们若是有一句半句不懂,必定把这句改掉。这正合于大诗家白香山做诗使老妪都解的故例。所以他虽不曾多读书,不多识字,我却承认他有文学心孔的人。”整个文风,明白如话,正符当年合胡适之、周作人等提倡白话文的要求。
细看全书,所用曲调偶有今天的清曲所没有的,如滩簧调、香火调。最有价值的是版权页,罗列了若干“校订者”的姓名,如裴福康、尤庆乐、王万青、黎子云、葛锦华、周锡侯等,均为一时清曲翘楚,也可知作者的确曾将其唱词交给这些清曲家试唱。印刷与发行者是薛泰昌铅石印刷局,地址在左卫街(今广陵路),每册定价大洋一角二分,都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。这对于研究扬州近代的印刷史,也是罕见的材料。